人心没有着落处
人心没有着落处
李义奇 2024-11-04
天
李义奇
时间:2019-10-28
天命与民意的结合,将政治的意义,由不可知的神与天,引向可知的世俗人间,开启了新的文明。但天命观也导致了道统与政统的分离。所谓道统,简单讲就是社会应该是怎样。所谓政统,简单讲就是社会实际上是怎样。
千百年来,中国其实就是一个赤裸裸的世俗社会。几千年的中国,政统妥妥贴贴地降服着道统。形式上高高在上的天,实际上匍匐在世俗权力之下。人类幻想的天庭,原本是人世间意识的反映。古往今来,概莫如此。


天,对于中国人而言,是极其重要的概念。即便是现在,华人无意识间的呼唤,“天啊”与“妈呀”,几乎也是可以相互替换的两个词汇。中国人的“天”,与外国人“Oh, my God”有相同,更有不同。外国人呼唤“上帝”,是后天习来的;中国人呼唤“天”,是先天的遗传。外国人的“上帝”,指向是惟一的明确无疑的,而中国人的“天”,很多时候是暧昧不清的,甚至正在呼唤“天”的人,也有可能没搞清楚,他嘴里或者心里的这个“天”,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再之,作为普遍的文化习俗或者说是信仰,中国人的“天”,比外国人的“上帝”,早出现了一千多年。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论述过,中国人的“天”,有五种含义。一是与地相对应的物质之天;二是有人格的主宰之天,类似于上帝;三是运命之天,指人生中个人无可奈何者;四是自然之天,指四季更替,自然运行之规律;五是义理之天,指宇宙中最高的原理。他又说,古籍中所谓的“天”,除物质之“天”外,大多是指主宰之“天”,如同西方的“上帝”一般。但是,也有不同意见,如张岱年先生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论语》中的“天”既有主宰义,又有自然义。“天”的含义,的确不易区分清楚。
公元前一千多年,周武王经牧野之战而灭商。是时,周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远不及商。周武王顺应时势,抓住时机,以弱灭强,得以取代商朝自立。西周为了坐稳江山,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做出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在政治和组织形态上,以血亲和姻亲为纽带,实施封建,推行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领域,西周创制了“天命论”,以取得众多诸侯的信服。他们说,“天命靡常”,能使国家兴起,也能使国家衰亡。夏朝失去天命,由商取代,商朝失去天命,上天就选择周代商而立。是上天的意志,对商纣的暴虐统治不满,才收回其统治权并赐予西周。因为周能够敬天、孝祖、保民,民心在周,所以上天将天命交付周。故弱小的周能够抓住机会,一战而胜,取代商朝。一切都是上天的选择。
《尚书·康诰》有“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天命,越厥邦厥民。”大意是说,天降大命于文王,要他灭掉殷商,承受天命及其土地人民。
“明明上天,照临下土”。
“高高在上,日监在兹”。
周人为什么想到借用“天”这一概念呢?或者说,周人为什么崇拜上天呢?许倬云先生在《西周史》中有一个解释。他说,先周时期,周人活动的区域陕甘黄土高原西半边,黄土有“自肥性”,即通过灌溉可以把底层养分不断地吸收到地表,适宜农耕(农耕是当时生产力水平最高的生产方式)。不利的因素是,与秦岭汉水区域相比,黄土高原西半边地势高亢,降水量较少,农耕丰歉主要看上天能否及时足够地降下甘霖,先周人自然就以为,他们的幸福生活取决于上天的态度。同时,由于地形地貌的原因,先周人每时每刻看到的是晴朗的、笼罩四野的、一直到视线尽头的长空,而这完整而灿烂的天空,无所不在,高悬于上,俯视着人们,保护着人们,自然就具有那种慑伏人心的力量。那时人们心中的天,是最大的全体,人们无论是躺下或者仰望上天,天都是人们能够见到最大的东西,没有比天更大的了。
西周之前的传说中,多有东方的帝与西方的天冲突争斗的故事,虽传说中胜利多归属于东方的帝,但是,这些传说,如“刑天舞干戚”等,也印证了天神崇拜的西方专属性。周人姬姓,曾经讲过,我姬姓出自天鼋。周王自称“天子”。这些都可说明,周以天为图腾,以天为本族宗神。
西周确立的文化制度,一直影响到现在。可以说早期文化东西激荡中形成的华夏文明,稳定凝固在西周制度体系之上,如周礼、宗法等。后来儒家搞的那一套,就是要恢复“周公之制”。这些按下不提,我们只讲“天”。
后来学者多认为,周朝发明的天命观,其意义不仅在于说服诸侯心服口服以周代商,还在于告诫他们的子孙,一切保天命的办法,都在人事之中,“祇若兹德,敬用治”。天命在于人心所向。“受命于天”,“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天命与民意的结合,将政治的意义,由不可知的神与天,引向可知的世俗人间,开启了新的文明,将史前文化带入文明,这是中华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其意义是开天辟地的。
我们不否认天命观的意义。但是,后来历史的走向,也提醒我们,不要高估了天命观的实践意义。就像行走在污浊的世间,不要太依靠人们自觉自愿的道德自律一样。
西周在创制天命观收服人心的同时,他们可能没有预料到,天命观的副作用,是道统与政统的分离。所谓道统,简单讲就是社会应该是怎样。所谓政统,简单讲就是社会实际上是怎样。
西周以前,是政、教合一的。君王既是俗世的统治者,又是上天的代表。因为君王垄断了与上天沟通的渠道以及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权。早期的君王就是巫,巫作为氏族首领和部落大祭司,掌管一切神人之事。后来巫分化出来,君王专门设置负责与上天沟通神职官位,也称“巫”。因为巫与王一体,如果需要,君王可以根据自己的行为或自己想要的行为,提供一套解释,以收服人心。
西周创制天命观后,情况变了,道统有了一整套固定的标准,且可观测。天意从不可知变为可观测,人世君王随意解释天意的权力受到极大限制,再也不能根据行政(统治)的需要随意解释天意了。结果是政统与道统分离。
政统与道统分离后,后世的儒者从政统里分离出来,成为影响政事渐微的卫道者。君权不断集中的过程中,抱有淑世情怀的儒者一直尝试,用道统影响控驭政统。儒家孜孜以求的王道,就是要求政统依照道统的规范行政。
春秋战国时代,大争之世。儒家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在这样的时代里,终不济于世。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武帝的打算,是利用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为其治理国家和开疆拓土提供意识形态方面的支持。但是,独尊儒术以后,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发展壮大,他们用道统影响控驭政统的理想,开始萌动。
历史上争夺统治权力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尽管政权都是战场上血淋淋的砍杀而来,但“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统治者需要民众臣服,需要改造思想使他们从内心服从,需要道统对政统的认可与支持。皇权需要儒,政统需要道统为其统治的合法性提供背书。心怀淑世理想的儒家,借势为承继道统努力抗争。这里面的代表人物,就是向汉武帝倡导“独尊儒术”的一代大儒董仲舒。
儒家典籍中有不少灾异现象的记录。这些记录,在天命观思想的指导下,大多与君王执政得失联系起来。例如《左传》中晋平公与士文伯有一段关于日食预兆的对话,“国无政,不用善。”导致日月之灾。熟读儒家经典的卫道士董仲舒,显然知道借用自然天象弘扬道统的重要意义。他编写了《灾异之记》,把古今灾异现象,用《公羊》思想加以推演和解释。董仲舒说,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如奢侈过度、刑罚失中、赋役太重、任人不当、后宫不肃、违礼乱制、穷兵黩武等。董仲舒说,纵然皇帝是天之骄子,具有至上的君权与独尊,也不能为所欲为。皇帝必须服从天意,天若不满皇帝作为,会降下灾异予以示警。同时,他认为只有儒生有本领解释上天的意旨。世俗的皇帝必须借助儒生领悟天意。
当时辽东高庙发生火灾。酷吏主父偃就将董仲舒的灾异书给了汉武帝。武帝召集学者官员讨论,大家都认为此书讥讽朝政。结果是董仲舒下狱,论罪当死。后来被汉武帝特赦。此后,他再也不敢言灾异了。但是,灾异论却流传了下来。
儒家不是铁板一块。当时几与董仲舒齐名,同样治《春秋》的儒者公孙弘,也是一个代表人物。公孙弘出身低微,放过猪,是个猪倌出身。年40余乃从胡毋生学《公羊传》,与董仲舒同治一经,算是同业。建元元年武帝诏举贤良,他应征对策,被录为博士。后历内史、御史大夫,位至丞相。史说公孙弘为人善谀,曲学阿世,朝会议事,从不面折廷争。他曾与汲黯等相约议事,等到武帝面前,尽背前约,一切顺从皇上旨意。天子见他为人谨慎,辩论有余,但又不迂腐不过激,且熟悉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遂大悦之(《史记·公孙弘传》)。
在儒者中,他是善谀者;在善谀者中,他是儒者。明习儒学,满足了武帝好文的爱好;善于吏事,具备为官的能力;阿事善谀,满足了人君的虚骄心理。故为官累迁,位至宰相。公孙弘这种人,没有原则,揣摩上意,不守信用,出卖朋友,沽名钓誉,阴结死党,以谋取高官厚禄为人生目的,可谓后世为官者的先祖。在公孙弘开拓的儒者做官的路线上,周公、孔子及其追随者所竭力维持的道统,从规范政统沦落为支持皇权的工具。
西汉后来仍盛行言灾异,不过,皇帝已经成为灾异说解读裁判者的角色。灾异成为皇帝责备、左迁官员的借口。上层官员对灾异负责,在汉代已经成为一个传统。《汉仪注》上明确写着,灾异发生时,丞相应该主动辞职。
革命从来就不是请客吃饭,卫道的儒家,后来思想滑坡,自甘堕落,沦为走狗,甚至落水狗,也是自然而然。读书人只有能屈服于皇权,才能获取安全。顾炎武是明朝的官员,改换朝代后,他禀承儒家卫道传统,不再出仕,闭门读书。但为了个人和家族安全,他不得不派三个外甥(著名的“昆山三徐”)去朝中做官。舅舅读书传播革命的种子,外甥做大官维护政统,表面矛盾,实质上统一的。当时代最优秀的读书人顾炎武,尚且如此,其他的儒者,只能退而求其次,渴望成为政统的奴仆了。
千百年来,中国其实就是一个赤裸裸的世俗社会。权力的背后是利益,利益决定一切,对思想不屑一顾。几千年的中国,政统妥妥贴贴地降服着道统。形式上高高在上的天,实际上匍匐在世俗权力之下。或者说老百姓心中所想口中所念的“天”,实际上就是最高权力的代指。
西周开国一千多年以后,西汉董仲舒后大约三、四百年,在西方古罗马帝国,同样发生着神权与世俗政权之争。当耶稣说“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时,西方也是并行着类似的两个权力系统。
基督教出现后,在基督教义中,代表上天的神,变为惟一的上帝(原来古罗马信奉众神)。一开始,基督教一直受到世俗政权的镇压和无情打击。事情到君士坦丁执政时出现了转机。公元313年,罗马西方正帝君士坦丁与东方正帝李锡尼,在米兰发布了“米兰敕令”,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公认的宗教之一。此后不久,君士坦丁将皇帝私人财产捐赠给基督教会,君士坦丁本人因此被基督教称为“大帝”(The Great)。临终时,君士坦丁受洗成为基督教徒,君权向神权低下头颅。
有个背景知识需要交待一下。公元前31年到公元180年200多年间,罗马一共有16位皇帝。与之相比,3世纪235-284年这50年,罗马帝国一共产生了22个皇帝,平均每2年多就换一个皇帝。时间最短的是昆提里乌斯,在位仅仅17天。更换最频繁的是238年,一年间换了5位皇帝。原因在于,古罗马元首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不满意就可以更换执政者。当时影响元首权力更迭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兵变。士兵们已经习惯于按照他们的意愿随意弑杀皇帝,如同儿戏。甚至“罗马人把当皇帝视为畏途,因为一个人如果被近卫军拥立为帝,就等于是被判了死刑。”
聪明睿智、具有超人政治智慧的君士坦丁,认识到把赋予君主统治权的对象,由“人”转为“神”的有效价值。因为委托和剥夺统治的权力,由可知的“人”转为不可知的“神”后,可知的人,再也无权置喙君权。当时,多神教中的罗马诸神不适合扮演这种角色,因为罗马诸神只是护佑人类,而非指点人类如何生存。只有一神教基督教满足君士坦丁对“神”的需求。双方一拍即合,君士坦丁利用基督教建立了“君权神授”体系,为自己的君主世袭制正名,确立了血亲世袭继承制度,最终确立了罗马帝国的君主专制政体。
君士坦丁大帝支付的对价是,俗世政权匍匐于上帝神权之下。接下来是众所周知的,历经千年的黑暗中世纪。西方的历史,为道统政统之争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高昂的。
起点不同,事物演化的结果自然不同。中国的道统降服于皇权政统之下,与古罗马君士坦丁后政权降服于基督教上帝神权之下,都是利益斗争与妥协的结果,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尽管西方的“上帝”比中国的“天”晚出现一千多年,但是,历史上曾经的表现,“上帝”对世俗政权的权威,远远大于中国的“天”。
过刚者易折。“上帝”再强,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西方文艺复兴的成功,以及后来现代民主社会的建立,他们需要反对或抵制的是一个虚拟的上帝,是一个无法在阳光下凉晒示人的上帝,自然就会容易一些。不像东方社会,需要打破和抵制的,从来都是硬梆梆的现世权力和利益。
两千年过去了,“上帝”也好,“天”也好,对世俗权力的符号和象征意义,基本上不存在了。但是,东西民众的心中,还是为它们保留了位置。紧急时刻无意识的呼唤,天或者上帝,还是会脱口而出。
天,永远都是那个天,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人类幻想的天庭,原本是人世间意识的反映。这一点,古往今来,概莫如此。如果人们感受到不同的天,只是人世不同了,而已。
●新 书 推 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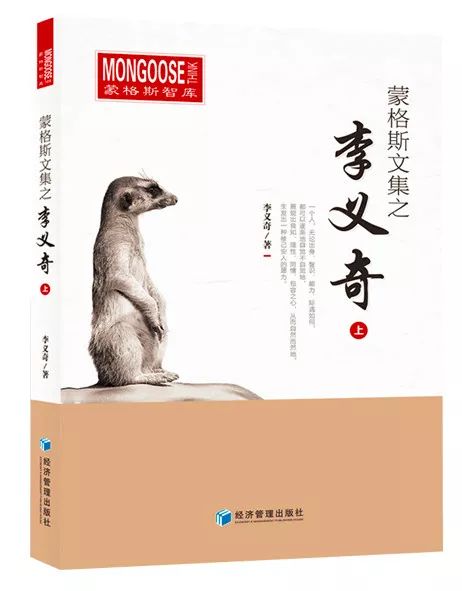
《蒙格斯文集之李义奇(上)》
李义奇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内容简介
《蒙格斯文集之李义奇(上)》这本书主要收录了李义奇先生在金融、历史、社会原理、改革开放四十年、读书笔记、随笔杂谈等领域系列文章,其理性、尖锐和功力将一一展现给各位读者。
现此书已开始售卖,书籍售价为76元人民币,欢迎各界人士购买!此文集分为上、中、下部,总计约60万字,将在半年内陆续推出,届时将优先通知上部购买者。《蒙格斯文集之李义奇(上)》购买请扫蒙格斯商城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