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银行公司治理的“卡夫丁峡谷”
有效的银行公司治理做法是获得和维持公众对银行体系信任和信心的基础,这是银行业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稳健运行的关键所在。
朱小黄 2019-11-01
如何避免不必要的恐惧
格尔德·吉仁泽
时间:2019-1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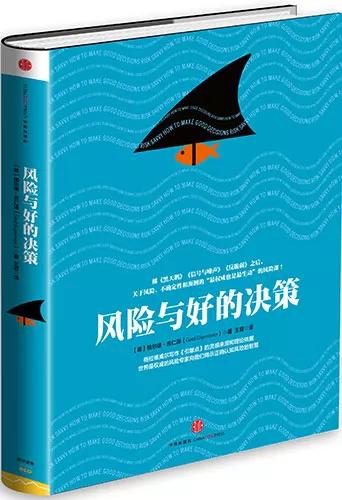
本文摘自《风险与好的决策》一书
格尔德·吉仁泽 著
中信出版社
社会模仿:害怕别人所害怕的事物
很多欧洲人都对吃从森林里采的蘑菇司空见惯,但美国人却不赞同这种鲁莽的做法。美国私有枪支的数量比美国民众的人数还多,但欧洲人一想到邻居醉酒后可能拿着枪惹是生非,就会心惊肉跳。为什么不同的人会害怕不同的事物?文化差异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共同的心理,而且它不是建立在直接经验的基础上。尝试吃每种蘑菇、接触每条蛇或每只蜘蛛,从而判断它们是否有毒,这种方法并不可取。我们的心理会保护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不犯致命的错误。正如那句名言所说,愚者只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智者则从别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这种智慧暗含着一个无意识原则,即通过社会模仿来了解恐惧。
别人怕什么,我们就怕什么。
如果亲身体验可能让我们丧命,那么这个简单的原则可能会保护我们,也可能会让我们害怕本不该害怕的事物。不过,害怕不该害怕的事物总比遇上致命的危险好得多,经历两次虚假的警报也比一次遇险好得多。
不同文化所展现的怪诞的恐惧心理,为各地游客提供了津津乐道的奇闻逸事。但是,随着社会流动性的提高,不同的文化已不再孤立。因此,差异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它只是一种普遍的趋势,而且一种文化中也可能会出现巨大的差异。
文化差异是人们害怕某物或对某物放心的原因。人们不会完全喜欢或厌恶风险,原因在于社会学习。他们会害怕同伴害怕的事物,因此有的风险他们敢于承担,有的风险他们会极力规避。
但是,社会学习并不是我们了解恐惧或寻求心安的唯一方法,还有一种方法是生物性准备,它能让我们快速“学会”对人类进化史上的危险情况产生恐惧感。
生物性准备
为什么孩子会害怕蛇和蜘蛛,即使他们国家的毒蛇与毒蜘蛛已经灭绝?这看起来似乎很愚蠢,但是他们的这种恐惧还是有理论依据的。通过个人亲身体验去认知某种动物是否致命,可能会丢掉性命;通过社会模仿来学习,也许又过于缓慢。于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习得了第二个学习方法,即巧妙地集先天与后天于一身。恐惧的对象已在基因程序中“预设”好了,只需要被输入的社会信息激活即可。
爸爸害怕蜘蛛,女儿也害怕蜘蛛。
生物性准备是指威胁我们祖先生命安全的事物或环境,比如蜘蛛、蛇和黑暗。举个例子,一位爸爸发现自己胳膊上有只蜘蛛,因此大叫起来,他的女儿恰好看到了这一幕,这足以让她习得这种恐惧。但是,当这个小女孩看到祖母对手枪、摩托车以及其他可能致命的现代发明感到害怕时,她并不会很快习得这种恐惧。让孩子对蜘蛛产生恐惧,要比让他们害怕电源插座容易得多。通过生物性准备来习得预设的恐惧,其过程如下:
预设的恐惧→其他人表现出这种恐惧→习得这种恐惧
与通过试错法学习不同,这种预设的恐惧人们很快就能学会,往往一次即可。一旦学会,便很难改变。人类的很多恐惧都早已在基因中预设好了,其中包括害怕动物(如蜘蛛、爬虫),害怕物品或事件(如空旷的露天场所),害怕某些人(如面目狰狞或反社会的人)。动物之所以在人类的恐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很可能源于我们的祖先防御食肉动物的生存需要。生物性准备让人们知道该害怕什么,而无须亲自冒险体验。
生物性准备让我们学会对旧的危险产生恐惧感,而社会模仿则让我们学会对新的危险产生恐惧感。
自控力是对抗焦虑情绪的最佳利器
目前,很多国家的人们似乎都越来越担心工作、人身安全以及社会对他们的认可度。我们是否进入了焦虑时代?据说,数十年来,美国的年轻人越来越抑郁。当研究对象为不同年龄段的人群时,20世纪初出生的人中仅有2%的人表示自己患有严重的抑郁症,这一数字在20世纪中期出生的人中却高达20%。这一差距可能只是表象,并未反映真实情况。年老的人会存在选择性记忆的情况,他们想起来的可能主要是年轻时的美好时光。为了避免这种可能性,可利用群组对比的方法研究同一年龄段的年轻人,并对其进行追踪研究。
现在的年轻人变得更加焦虑了吗?
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MMPI)是用来鉴别精神疾病的一种人格测试,它可以检测包括疑病、抑郁、分离性障碍等心理疾病。为了进行历时比较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起,美国有成千上万的儿童和青少年做了此项测试。
测试分数的变化十分惊人。1938~2007年,大学生的临床量表分数稳步升高,尤其在情绪多变、不安、不满、不稳定方面(所谓的F量表)。分数越高,这些性格特征越突出。我们以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大学生的平均分数为基准线,最近几代人中,几乎所有的学生——确切来说,有94%的学生——的测试分数有所提高。不切实际的积极自我评价、过度活跃、自控力低等方面的分数也在提高。在该测试的所有量表中,85%的学生的分数高于基准线:更自恋,更以自我为中心,更反社会,更担心,更悲伤,更不满。根据学生的自我表述,这就是近几代美国年轻人的心理状况。曾被视为异常的情况现已成为常态。
这种情绪变化的原因何在?也许是现代化的大学让学生变得喜怒无常、紧张不安,他们第一次离开家,压力倍增。但是,高中生也经历了类似的情绪变化,而且男生和女生之间以及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之间并没有差别。对此可能有另外一种解释:如今,抑郁或紧张的情绪是社会的一种需要。虽然这可以解释其中的一部分变化,但整体趋势并没有变。也许原因是经济方面的:心理状况可能会随着经济大环境的起伏而变化,从大萧条时代直到今天。但是,测试分数的升高与经济变化或失业率基本无关:年轻人的分数增长很平稳,并没有随着经济周期而波动。在“二战”、“冷战”以及动荡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儿童焦虑和抑郁的比例实际上还比现在低。
内部控制:专注于技能而非外表
最佳解释可能与年轻人认为生活中什么最重要有关,这体现在内部目标和外部目标的区别上。内部目标指通过提高自身的技巧、能力和道德价值观,使自己变得更成熟,从而过上有意义的生活。外部目标则与物质奖励以及他人的看法有关,包括高薪、社会认可和美貌。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们的目标变得越来越外部化。针对大一新生的年度调查显示,近几代大学生认为“经济富足”比“生活有意义”更重要,这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的情况恰恰相反。
这一变化使得年轻人在达成目标方面很难做到自我控制,因此他们的情绪和行为也越来越失控。内在——外在心理控制源量表(IELCS)是一种调查问卷,可以用来测试人们对自己可以掌控命运的相信程度。1960-2002年,调查人员给9-14岁的儿童做了这份问卷。结果表明,多年以来,儿童对自己可以掌控命运的相信程度大幅下降。2002年儿童的外部控制倾向要高于1960年80%的儿童。如果儿童很少进行内部控制,面对不确定性时他们往往会焦虑不安:我一定会失败,尝试没有任何意义。
相反,擅长进行内部控制的人往往生活得更好。他们在社区里更加活跃,更注重自己的健康,并且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我们也许无法控制别人对我们的衣着、技能或外表的看法,但是,我们可以控制学习语言、弹奏乐器、承担照顾小孩和老人的责任等内部目标。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尝试重新专注于内部目标,摆脱对日常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过度焦虑。

跨越银行公司治理的“卡夫丁峡谷”
有效的银行公司治理做法是获得和维持公众对银行体系信任和信心的基础,这是银行业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稳健运行的关键所在。
朱小黄 2019-1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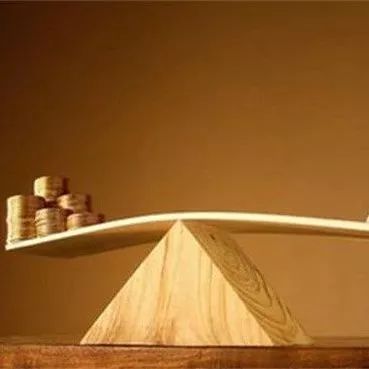
用简单法则应对充满未知风险的金钱世界
当危机近在咫尺,你对自己的钱财和未来忧心忡忡时,该怎么做?把头埋进沙堆,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等待专家来解决问题?如果这样做,你可能会看到更多的官僚主义、更多的科技、更少的个人自由,但却看不到能正视不确定性的公民。
格尔德·吉仁泽 2019-11-01

风险厌恶与防御性决策
风险厌恶与担心犯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果你是公司的中层管理者,你可能总是担心自己会犯错,并因此受到责罚。这种氛围对创新无益,因为想创新就得在前进途中不断冒险和试错。
格尔德·吉仁泽 2019-11-01